2025 羽球团体赛半决赛:黄雅琼领衔逆转,刘洋名宇复仇点燃全场!
6 月 14 日,2025 全国羽毛球团体冠军赛混合团体半决赛在沈阳体育馆掀起热血对决,两场半决赛堪称 “技术与意志的双重盛宴”。浙江队与辽宁队的焦点战中,黄雅琼领衔的混双组合率先亮剑,孙超与辽宁新星刘洋名宇的男单复仇战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沸点;湖南队则在与江苏队的五场鏖战中,凭借双打 “绝地反击” 锁定决赛席位。以下是不容错过的三大高光时刻:
一、黄雅琼 “定海神针”,混双奠定胜局
作为浙江队的 “王牌开场”,廖品逸 / 黄雅琼组合面对辽宁队许嘉赫 / 崔逸格时展现了绝对统治力。首局比赛,黄雅琼在后场精准调度,廖品逸网前封网如铁闸般严密,两人以 21-13 轻松拿下。次局辽宁组合加强进攻,一度将比分追至 18-20,但黄雅琼关键时刻连得 3 分,以 23-21 终结比赛。场边观众惊呼:“黄雅琼的网前假动作晃得对手找不着北!”
PG官方电子,pg大满贯,pg平台电子网站,pg电子官网站,pg.qq.com二、刘洋名宇三局鏖战复仇,男单掀翻 “卫冕冠军”
这场半决赛的最大看点,当属辽宁队 19 岁小将刘洋名宇与浙江队孙超的男单对决。此前 4 月的全国单项锦标赛决赛,孙超曾以 2-0 横扫刘洋名宇,但此次半决赛,刘洋名宇展现了惊人蜕变:首局他以 21-18 先声夺人,次局孙超凭借经验以 21-15 扳平。决胜局中,刘洋名宇在 18-19 落后时连得 3 分,以 21-19 完成复仇。当最后一记扣杀落地,沈阳主场瞬间沸腾,连解说员都激动呐喊:“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!”
三、湖南队双打 “心脏战”,决胜局逆转点燃全场
另一场半决赛中,湖南队与江苏队的对决堪称 “体能极限挑战”。前四场战至 2-2 平后,决胜场男双成为生死战场。湖南组合张滨榕 / 刘适文在决胜局一度以 12-15 落后,但两人突然爆发:张滨榕后场重杀连得 5 分,刘适文网前封网如影随形,最终以 21-15 逆转获胜。现场观众回忆:“最后 5 分钟完全不敢眨眼,这就是羽毛球的魅力!”
四、浙江女单 “00 后” 一剑封喉
当浙江队与辽宁队战至 2-1 时,19 岁的陈奕诺迎来 “定胜时刻”。面对辽宁队陈昕彤,她在首局 16-16 后突然提速,连得 5 分以 21-16 拿下;次局更以 21-18 锁定胜局。赛后陈奕诺表示:“教练告诉我要像‘小钢炮’一样冲击对手,今天终于做到了!”
结语:

两场半决赛不仅是技战术的较量,更是年轻选手证明自我的舞台 —— 刘洋名宇的复仇、陈奕诺的稳定、湖南双打组合的抗压能力,都预示着中国羽毛球新生代正在崛起。6 月 15 日,浙江与湖南将争夺冠军,而辽宁与江苏的季军战同样值得期待。这届赛事再次印证:羽毛球的魅力,永远藏在每一个 “下一拍” 的无限可能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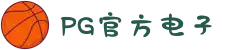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